三教一般指儒释道。儒释道,“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
三教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三教一般指儒释道
南梁
儒教、佛教、道教
元明清三教合流
基本解释
三教:佛教传入我国后,称儒、道、释为“三教”。
引《北史·周本纪下》:“十二月癸巳,集羣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唐·牛肃《牛应贞》:“学穷三教,博涉多能。”
明·陶宗仪《辍耕录·三教》:“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穀於世,岂可一日闕哉!’”
鲁迅《华盖集·补白二》:“佛教初来时便大受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1
进程概括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直到元明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后汉初期,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得以在中华大地渗透普及。这期间,相距了数百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弘明集·道安传》里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四百余年才开始真正被中国人接受,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当时华夏在文化上极为自信,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

一般说来在这时期扬佛教抑儒道的风气相当浓烈。活跃于东晋至刘宋时的宗炳认为佛典宣说的思想无论较儒家的《五经》,还是道家的《老子》、《庄子》,都更为精妙。其《明佛论》说: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
这是说佛经不但涵摄儒书、道典的优点,而且还远较二家更为殊胜。正是居于此,魏晋南北朝的崇佛者又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为“大圣”。这种独崇佛教、贬抑儒、道的态度在梁武帝身上达到顶峰。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道二教都斥为邪教,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隔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虽然佛教很早就传入,然只在少数信奉者范围内流传。这样前后经历了约五百余年的时间。在各种因缘的配合下,渐次坐大,各类佛学思潮不断涌现。迨至隋唐时代,已进入实质性的综合创新时期,佛教佛学,一并繁荣。不独在所有外来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与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亦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乃有问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资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张将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后面。如智颉(538—597)《维摩诘经玄疏》引《造立天地经》云:宝应声闻菩萨示号伏羲,以上皇之道来化此国。又引《清净法行经》说:摩诃迦叶应生震旦,示名老子,设无为之教,外以治国;修神仙之术,内以治身……光净童子,名日仲尼,为赴机缘,亦游此土,文行诫信,定《礼》删《诗》,垂裕后昆,种种诸教。
智颚引用这两部伪经,贬低孔子、老子,甚至连创作八卦的伏羲也不放过,意在显示佛教在思想领域的实力,反客为主的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再像三论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也认为儒、道二教皆为“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至于唐代撰写《广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归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宣称: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唯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故夸门学日盈,无国不仰其风;教义聿修,有识皆参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为尊。
这种昂扬的自信源于佛教徒文化自信心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佛教也非常重视人才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重视培养大量人才的结果就是涌现大量的人才,之后是各大宗派的相继崛起,隋代的天台宗、唐初的三论宗、法相宗、则天武后时的华严宗、开元年间的密教、唐末的禅宗等,人才辈出,大部头的佛学专著也不断问世。

虽然,此一时期僧尼的人数并不很多,终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但因为多数僧尼的文化素养奇高,其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连唐太宗也不敢漠视,尽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但也不得不承认佛教潜在势力的雄厚,如在贞观11年(637)的一则诏书中说:
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国。……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光,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滋累代。
此种说法决不是一般的虚拟之词,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以隋代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这些数据虽有夸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兴佛功行已不难想见。同时,佛教义学的研究也相当繁荣。隋末唐初的战争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损,但佛教的根基并未动摇,唐太宗的感叹不是空穴来风。至于间里民众的虔诚信仰,更是佛教流风不堕的社会基础。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材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
至于“风靡于朝廷”的见证,也同样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实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书请除去佛教,当其疏交付群臣详议时,大臣多袒护佛教,支持傅奕的,不过太仆卿张道源一人。连太子李建成、李元吉都为佛教说情,可见佛教在朝廷中的影响程度。
这是佛教问鼎政治地位的又一资本。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对朝廷“道先佛后”的政策提出异议,从而引发佛、道两教之间政治上的“排座次”之争。虽屡遭失败,却也说明佛教既然已从原先依附于儒、道二教的阴影中走出,转变为与道教的矛盾,其势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于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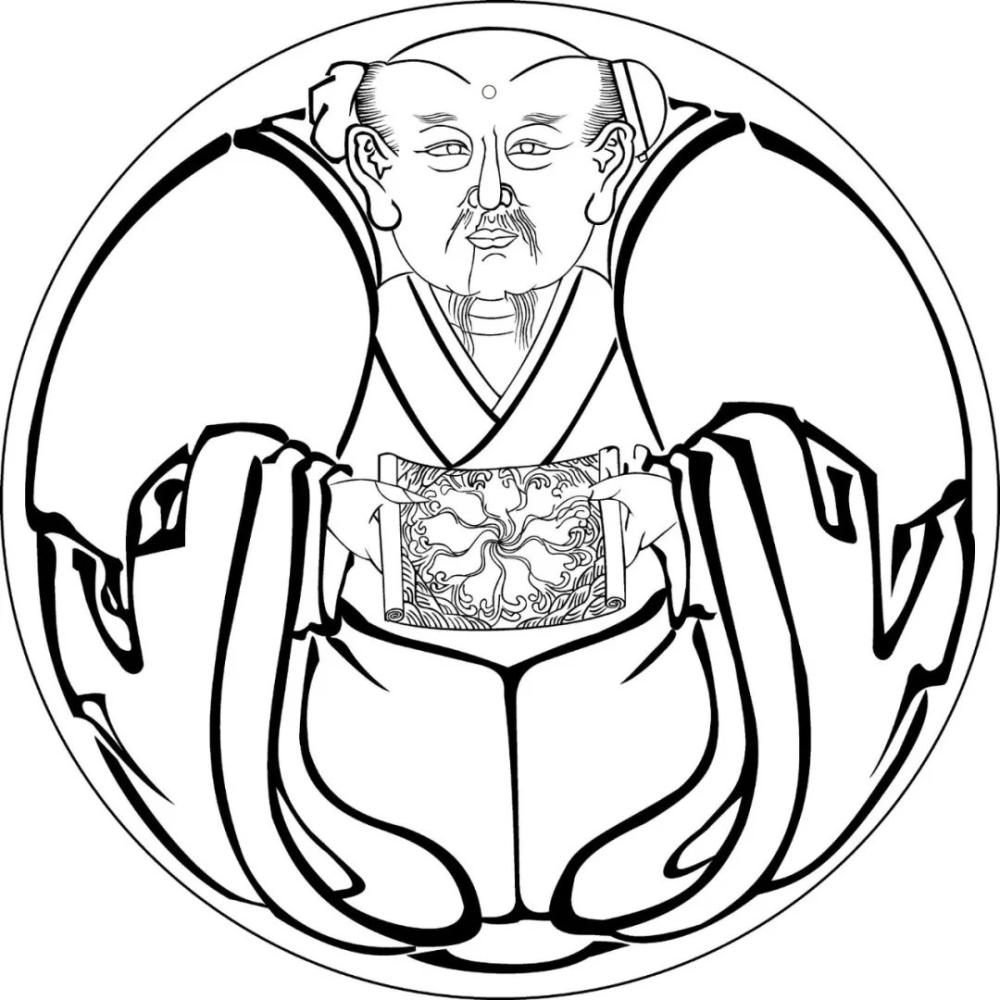
与此同时,佛教还处处主张与道教划清界线,此与魏晋时期高僧多以老庄诠释佛教,比如僧肇著论,即盛引老庄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佛、道二教的门户之见,虽初起于道安时代,如名士习凿齿《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中说:“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意指道安(312--385)视道家不过是“方中驰骋”而已,没有佛家的境界高远。但当时并未出现相互诋毁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相互取资,亦复不少。隋唐以降,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其进击性日趋强烈。因此,急于与道教分河饮水,为坐上三教领袖地位而扫除障碍。
所以能在佛学领域里开出一片新天地来。而道教则没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渐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视、奚落,以至于让当时的世人产生了看佛书,以后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经书的思想。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论争几大主题进行逐一梳理。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的交锋。由于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对中国以现世主义为中心的伦理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因此中国人在初次遭遇这种异质文化冲击时的确感到心灵的巨大震撼。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遭遇的首次挑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主动挑战的过程中,对佛教采取的开放、接纳、改造的系列姿态,使得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从而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公元十二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中国反而代之而起成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为中国人提供了来世、轮回、地狱等抽象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
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我国邻近的国家。
在印度佛教未传入之前,儒学占有显著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在社会风气上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荦荦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和元朝时对道教的毁经灭藏。
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在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涌现大量本土宗门,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
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哲学思想。
在佛教理论方面,汉传佛教融汇了中国儒道文化的要素,成功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东汉时期佛教初传,为了让中国人能看懂佛典、理解其中义理,当时的译经者采取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等学说的词汇与概念,来解释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及思想,此谓格义佛教。格义佛教虽然会造成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却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重大意义。
两晋时期,一些僧人受玄学学派启发,力求融会贯通佛学义理,他们只求意达而不拘泥于文字,于是佛教般若学依附玄学而得以兴盛。他们既是中国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本土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也是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智慧的深入发展。此后汉传佛教的各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一直将中国儒家道家的心性论、伦理观等融摄到佛法中,有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华严宗宗密进而致力于“五戒”与“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将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的智慧推到一个高峰。明朝末年,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继续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融合了儒道思想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认为中国某些时期是“佛教的时代”(the Buddhist Age)或者说是“中国思想和信仰印度化”的时代(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and Belief);信仰印度化是中国之大不幸;“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轻易征服并统治了中国2000年。"(Hu shih, former Ambassador of China to USA, “India conquered and dominated China culturally for 20 centuries without ever having to send a single solider across her border.”)胡适在一篇题为《印度吾师》的文章中就这样说:“中国花了一千年才逐渐走出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征服,并取得某些程度的文化独立和思想上的文艺复兴。”所然有些夸大,但也可以从则面看出某些时期佛教的影响力。
《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中通过对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三教融合,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明代发展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明初期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中期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
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
明晚期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袁黄、李贽、屠隆、陶望龄、陶睾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李元阳、管志道、焦竑、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佛、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
陶望龄、陶睾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陶望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5《重刻法华要解序》。)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5《金汤外护名义》。)
焦竑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这显然说明,一至焦竑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备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王献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
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
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三教堂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
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禅宗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道教世俗化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简易平实,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不必绝俗离世,长往深山也"。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
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信,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而其下者,则流为巫公、师婆、火居道士,从事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火居道士,即道士中有妻室者。而道士之妻,则称"道嫂"。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动向,也已开始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如"苗贼作乱"时,火居道士李珍、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即为一例。
1.三教的意思·汉语词典-千篇国学

